【摘文】《艾瑪的記憶之書》第二封信
親愛的海曼:
雖然你在信中小心翼翼地掩飾,我還是發現你好奇極了,想知道那位長髮太太是誰。老實說,我的記憶相當模糊,過了這些年,我若是能稍微拼湊一些印象,是靠我姊姊的幫忙,她比我年長兩歲,比我記得多一點東西。
長髮太太叫做瑪莉亞。她相當年輕、高䠷和苗條;她從未跟我們講過她的家人或是她的人生,我們跟她的關係僅限於服從她的命令,不准抗議也不可以問為什麼。她是個嚴肅而且正經八百的人。
唯一會到家裡來拜訪的人是西昆迪娜太太,她在聖塔芭芭拉有家商店,她是瑪莉亞唯一的朋友,不過比她年紀大很多。每當西昆迪娜太太來訪,她們就會把我們趕到街上玩耍,命令除非她叫我們回家,不然不能回去。我們從不知道她們到底聊了些什麼。我們才剛剛埋葬雷伯勇將軍。我還穿著沾滿泥巴的衣服,我們通常穿著衣服睡覺,至於她只脫掉黑色長裙和鬆開頭髮。有一天,她一大清早叫醒我們,外頭還是跟夜晚一樣黑,她要我們三個一起去倒尿桶,然後再去打水,水桶和水壺都要裝滿。她則燒水、更換床單,並且把屋內僅有的四個家具擦得晶亮。
「脫掉衣服,我要幫你們洗澡。」
這是她第一次幫我們一起洗澡。我們三個光著身體站在鍋子旁,她很快地幫我們塗上肥皂,接著拿起木瓢,將我們一個一個沖乾淨。屋子裡的地面濕成沼澤地,都是泡沫;穿上衣服前,她要我們擦乾地面。她替我們穿上最好的那套衣服,叫我們三個坐在床沿,不能亂動。同時,她也換上最好的衣服,並仔細地梳理自己的頭髮,然後要求愛蓮娜把鏡子拿到她前面,跳蚤得端著蠟燭,要是有人晃動,她就會大發雷霆。當她打扮完畢,他要跳蚤去工廠看現在幾點。這一天,她沒給我們吃早餐,她忐忑不安,在屋子裡走來走去,彷彿一頭關在籠子裡的野獸。天亮了,她沒跟往常一樣開門,我們繼續點著蠟燭照明。忽然間,門口傳來三次輕柔的敲門聲,她在胸前畫十字符號,接著奔向前去開門。這一刻,有個非常高瘦的先生出現,他的打扮跟街區裡的人都不同,他就像我們在垃圾堆找到的報紙上出現的人。尤其是他戴了一頂暗色帽子跟拿著一把同顏色的傘,或許應該是黑色的。他舉起手擱在眉毛旁,似乎想適應燭光,他像是從門口飄進來,在她臉上印下一個吻,我們三個同時笑了出來。這是第一次有位先生踏進我們屋子裡。
瑪莉亞太太再一次鎖上門,拿著蠟燭取出一瓶酒,走向我們坐著的位置,先生板著一張臉跟在她後面,她把蠟燭靠近跳蚤的臉,對他說:「他是愛德華多,是你的。」他輕輕地摸了他的臉一把。
接著她向他介紹愛蓮娜,然後再介紹我。男人沒說半句話,一陣深沉的靜默蔓延開來。男人脫掉了大衣和外套,用指尖從背心口袋夾出幾枚硬幣,他給了愛德華多三枚,然後給我們女孩各一枚。「說謝謝。」瑪莉亞太太說:「現在你們到外面玩,不過留在門口附近,如果有鄰居過來,就告訴她我在睡覺。」
我們到外面時,感覺門上了鎖。那位先生待了很久。最後大門終於打開,瑪莉亞太太探出頭,確定沒人在看我們,她回過頭告訴他:「可以了」那位先生出來,步伐跟進門一樣輕盈,他經過我們身邊時,連看都沒看我們一眼,彷彿從沒看過我們。我們看著他大步遠離,身子挨著牆壁,彷彿怕被人看見。
當我們回到家裡,瑪莉亞太太正哭著,她清空衣櫃,挑出所有愛德華多的東西。她從床底下拿出一個紙盒,仔細地把挑出來的東西放進去打包。「愛蓮娜和艾瑪,妳們換上舊洋裝。愛德華多不用,你要跟我離開。」
她繼續哭著,我們也跟著哭了。當愛蓮娜替我脫衣服,我們看見桌上擺了一捆鈔票。我感到害怕,感覺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,我們通常只有硬幣,在家裡從沒看過鈔票。她沒解釋半個字,從盒子裡拿出頭巾,仔細綁在頭上,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就像教堂裡的聖母。
「你們別亂跑,我去找一下鄰居太太。」
她跟著鄰居太太回來,也就是跛子的媽媽,她給她看盤子和蠟燭在哪裡。她拿起裝著跳蚤的衣物的紙盒,走到我們面前停下腳步,告訴我們她要離開幾天,但是鄰居太太會過來替我們煮飯,因為沒人能照顧我們,所以她會鎖門。「乖一點。」她對我們說了兩遍,接著推著跳蚤到門邊,給他戴上海軍帽,要他一起離開。跳蚤睜大眼睛瞪著我們,眼淚開始不聽使喚。
我們關在屋內非常多天,我們失去感覺,不知道到底經過多少個白天和多少個夜晚,尿桶裝滿排泄物,我們開始使用鍋子。鄰居太太一天只來一次,她留下一大鍋玉米糊並叮嚀我們:「不要一次吃光,因為我明天才會再過來,吃完飯就吹熄蠟燭。」
我們又哭又叫,聲音驚天動地,鄰居紛紛過來趴在門板上安慰我們;我們盯著鐵片上的細縫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,渴望她的歸來。終於,有一天當我們靠在門邊的地上睡覺時,她回來了,這是我們第一次衝上去抱住她的脖子,開心地親吻她。她哭了出來,輕柔地把我們的手從脖子鬆開,再握住我們的手對我們說:「跳蚤不會再回來了。他的爸爸,就是那天來這裡的先生,是個偉大的政治家,或許以後會當上總統。他不希望他的兒子跟我在一起,他說他怕節外生枝,希望由他自己來照顧他;我帶他去杜哈,把他留在一間修道院,他的爸爸已經安排好一切讓他入住。」
少了跳蚤,我悵然若失,我哭泣,我尖叫,我呼喊著他,我不知道遠離波哥大是什麼意思。我相信如果扯開嗓子大喊,他會聽到我的呼喚。瑪莉亞太太看起來也非常悲傷,她變得更加沉默也更嚴肅。我想應該就是在這一刻,我跟愛蓮娜之間出現一種深深的祕密約定,一種我倆只屬於彼此的不自覺感覺。在當時,我不知道這輩子再也沒有機會再見到愛德華多,我不知道他後來的命運,我對他的回憶,只剩下那頂可笑的海軍帽底下那雙噙著淚水的大大黑眸。
艾瑪.雷耶斯
巴黎,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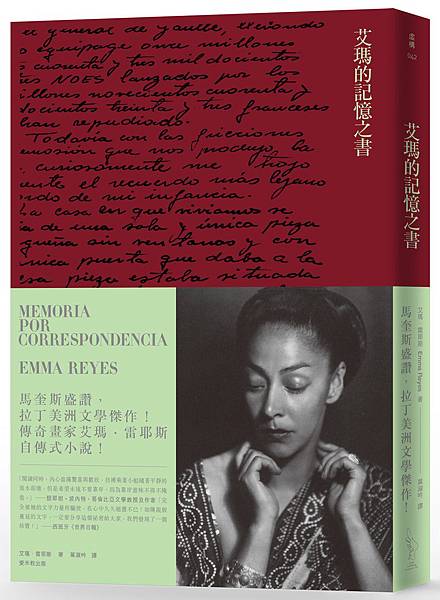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